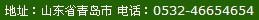|
微笑的故乡 ——王维娴 阴历十月朝,是传统的寒衣节,这在唐宋时期可是极为重要的节日,曾有“人间佳节惟寒食”的说法。在史书《旧唐书》中也有记载,唐玄宗下令“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由此可知寒食节祭扫先人唐朝就有了。依照祖辈沿袭的寒食节习俗,故此我们要回老家上坟。提前预知是收苹果的忙季,所以没有走镇上的路,而是选择了从村北进村。哪成想仍然被收苹果的浩荡队伍给挡得无路可走,不识路走错,绕成一条曲线,从村东回了村。如今看来,也不失是一个偶得。 村碑上赫然在目的几个熟稔的大字“夼沟村”,这是曾经最想跳脱的农村门槛,如今却让人看着生出几倍多的亲切感。村碑的背面还刻有名字的由来,据说是有一个传说典故的。相传,皇帝微服私访走到这里时,碰到了一条大蟒蛇,这村庄又是窝在山沟沟的地势,所以就给这里命名为“蟒沟村”,由于世世辈辈叫着叫着就“口误”成了“夼沟村”(或者是因为蟒过于吓人)。 这条路,当是进村的正大门,红红的十几个烫金大字,首先映入眼帘,这是村庄数年来摇身一变的“脱胎换骨”,这是几十年来村庄崭新的屹立于新时代的标签。镂架的铁工艺,像是村庄的一顶桂冠。最上面是“夼沟村”的门楣,然后是对联的眉头,“天下苹果第一村”,左联是“泉润三农源是党”,右联是“富兴万策本为民”。看到这儿,想必看官知道,我们村的大红苹果要带着全村的希望走向全国各地、走向世界各地,将更多的荣光记录在册。 进得村里,一座桥连起来了村东村西。东面有个像一把汤勺子似的水库,这个干涸了多年的水库,自从上次台风“梅花”,加上暴雨,上沿的河流游贯而出,竟然奇迹般地积存了满满的一塘水,微风吹来,闪着亮晶晶的波纹,像在极地游走的光芒。水库大满贯的水,像资源丰沛的钱塘江(当然没有大潮),穿过桥洞堂堂走出,顺次依循蜿蜒的小山夹道,流到曾经是天然浴场的小瀑布处。因为多年的干旱,泥土石沙垃圾瓦砾逐年递增了干裂河床的厚度,瀑布也早已失去了流光溢彩的当年不复记忆。 我们先回了一趟老宅,尽管老房子已经有了风烛残年苟延残喘的迹象,没人居住的房子,它似乎遗失了自己的使命感,又像是交接完了毕生的责任,没有了人间烟火的气息,周遭散发着霉乱潮湿的阴凉。老房子历经台风“梅花”的洗礼,更加岌岌可危了。东屋的墙体开裂了,潜进来一束明亮的光。屋顶的装饰棚纸无力地低垂——一条一条地耷拉着,像一个季节最后的恹恹气息,等待下一个轮回的交替。 出了老宅,向西。最令我讶异的,当属村子西北头的那个大深沟了。那里曾经在记忆里也是“风姿绰约”过的水库,在我个位数的年龄,它就已经开始了水位下降,上小学后,它已经不知何时彻底地干旱成了一个深阔的大沟了。我最深的关于它的记忆,是我和小伙伴背着大篓子,拿着大筢,去这个大沟里拾草,回家当引火。这些枯萎的青草,软软的,很适合当生火的柴草。如今用“水漫金山”毫不言过,几棵细瘦颀长的白杨树英伟地站在深水中,水平面已经跟树干细叉处齐平了,足有三四米的高度。看着这个蔚为壮观的“库存”,忽然有种梦里相逢的感觉,用力挤了挤眼睛,大水库还真在。 一路向北,路旁的果树上,红红的大苹果沉沉压枝低,每一个枝条都伸着细瘦的胳膊,好似再也无力托举了。远处的果园,更是一片一片的“中国红”,甚为壮观绮丽。我急急拿出手机,将这一排排硕果累累的丰收景象拍摄入我的镜头里。昔日,我们家的果园就在附近,那些多年的老树,可能早就被砍伐了。现在的果树也大都换了新品种,最多的当属红富士苹果了,其他的新品也叫不上来名字。最大的苹果差不多有一两斤的样子,真是诱人馋涎。记得看村里发出来的照片,一级级的展览比赛的大红苹果,不仅个头要大,还要“长相甜美”,色泽明丽,光滑圆润如红缎绸锦似的,咬一口嘎嘣脆,还能甜汁四溅。捧上获奖证书的果农,更是眉梢色舞,简直乐得合不拢嘴,睡觉都能笑出声来。听村里人说,在最干旱的时候,村里还给在山上免费挖了水井,供应浇果树,直接解决了影响最大的问题。加之村里人的辛勤劳作,所以我们夼沟村才有了无愧于“天下苹果第一村”的封号。数里方圆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农家都是靠果树作最主要的经济支柱,我们村也能与之比肩,村庄的富裕兴荣,让身为从这个村子里走出去的我们,也倍感殊荣。 村里的北山,一片静谧,除了风刮得树叶沙沙的声音。阳光仿佛困得打盹,山头上有阴呼呼的冷风,而四野俱静。在这忙碌的秋收季节,什么都给其让了路。但是怀念的仪式仍旧没有少,坟头的压纸一眼都能望见早已是新的颜色。 我们上小学是在村里,每年清明节,学校老师们,还有校外辅导员(一位退休的老党员),就会带领我们全体学生,穿着统一的校服(一般都是自家的旧衣服改造的),的确良白衬衣和深蓝色裤子,戴着鲜艳的红领巾,来给英雄烈士们扫墓。每年这位辅导员爷爷就会给我们讲一讲英雄的事迹,讲讲他们年纪轻轻就英勇牺牲的无私奉献的爱国精神,是那么深深地震撼着我们这些小孩子,我们不吵不闹安安静静地听着,回学校的时候我们长长的队伍也不再是叽叽喳喳而是静默无声。 十几岁时,天天走的沙土路,早换成了水泥路,最起码再也不会被土路粉饰成小泥猴了。那时候最讨厌骑自行车上下学了,好羡慕同学可以坐客车回家,好盼望有一条专车能通行到我们村口。这个还真的一不小心就实现了。自从有了乡线公交车,每天都有两趟车从村口的大牌子下面路过,所以村里的人哪怕种点蔬菜也可以去城里卖成了钱。现在收苹果的就在村里驻扎了,不用再像以前还要拉到镇上,或者送到收苹果的贩子那里,被品头论足般苛刻地挑挑拣拣,费很大的劲才能换回血汗钱。十月朝的时候,下(摘)苹果还不是大潮,所以这个收苹果的棚子还没有络绎不绝的景象。 大房(村委所在地)的大院子,可算是生活的焦点,每回村喇叭喊:夼沟村社员们,大房门口有卖猪肉的,快来买吧!然后,重要的话说三遍。大房,其实不光有村委会,还有村庄的休闲娱乐室。闲暇时间或者不忙季节,村里喜欢唱歌跳舞的乡亲,都迸发出了“声情并茂”的才艺。 农村老龄化是众所周知的社会渐进趋势时态,可是我们村里还是由为数不多的年轻生力军带动了整个村庄的发展动态,让村庄有了一脉热血沸腾的朝气,走向祖国繁荣昌盛的新时代。 宋朝诗人汪莘的诗《寒食节有感》中:寒食原头杜宇声,谁家不起古今情。纸钱烧罢人归后,一树梨花冻月明。寒食节带着前尘往事的记忆,走一遭老家,故乡的一草一树,山溪河涧,在这些抽象的跳跃的画面里,我仿佛看到了被夕阳染红的云彩里的村庄。 几日后,我发了个朋友圈:是不是应该感谢“梅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旱了四十年的水库,终于有水了。干涸的小河塘,终于溪水堂堂遑遑出走,瀑布飞溅。一个水源丰沛的村落,不负绿水青山,自带笑颜。 作者小介:王维娴,曾任《时代杂志》通讯员,报纸特约评论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散文学会会员、烟台作家协会会员、朗读协会会员。作品散缀《联合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北京劳动午报》《齐鲁晚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山东工人报》《大理日报》《北京茶社会》《家长杂志》《好家长杂志》《分忧杂志》《湍河文学杂志》《黄土黄种人杂志》等报纸杂志。读书与生活,像汽车的两个轮子,方向一致,向阳而生。 壹点号一垄诗意灵性 新闻线索报料通道:应用市场下载“齐鲁壹点”APP,或搜索
|
故乡山川微笑的故乡
时间:2024/3/8来源:本站原创作者:佚名
------分隔线----------------------------
- 上一篇文章: 最无用的2种汽车装饰,你都装了吗汽车品
- 下一篇文章: 新款丰田埃尔法还是不是有钱人的社交名片